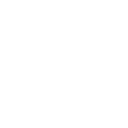——重庆鸽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诉重庆鸽皇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一审案号 :(2018)渝05民初3095号
二审案号 :(2021)渝民终166号
再审案号 :(2022)渝民申419号
1997年8月,重庆电线总厂与重庆电缆厂合并,改制成立重庆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1月,鸽牌公司设立,逐步托管、整合了重庆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员、财产,其企业名称沿用至今。鸽牌公司对“鸽牌”品牌做了广泛的宣传推广,获得众多荣誉,营收巨大。鸽牌公司拥有第146035号“ ”商标,由鸽牌公司的前身重庆电线厂申请,于1981年4月15日核准注册,核定使用在第9类的“电线”商品,2002年4月25日转让至鸽牌公司名下。该商标于2002-2014年期间多次被原重庆市工商局认定为重庆市著名商标,2010年1月15日被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此后,该商标在2018年期间多次在商标异议、商标无效程序及行政诉讼中被作为驰名商标进行保护,“
”商标,由鸽牌公司的前身重庆电线厂申请,于1981年4月15日核准注册,核定使用在第9类的“电线”商品,2002年4月25日转让至鸽牌公司名下。该商标于2002-2014年期间多次被原重庆市工商局认定为重庆市著名商标,2010年1月15日被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此后,该商标在2018年期间多次在商标异议、商标无效程序及行政诉讼中被作为驰名商标进行保护,“ ”商标在多个生效判决、裁定中被认定驰名的时间点为2008年1月开始至今。第3270081号“
”商标在多个生效判决、裁定中被认定驰名的时间点为2008年1月开始至今。第3270081号“ ”商标、第16039215号“
”商标、第16039215号“ ”商标均由鸽牌公司申请注册,核定使用在第9类“电线;电缆”等商品上。林某锋系鸽皇集团的发起人股东、首任经理,自2008年4月起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某锋于2005年3月7日申请第4524253号“
”商标均由鸽牌公司申请注册,核定使用在第9类“电线;电缆”等商品上。林某锋系鸽皇集团的发起人股东、首任经理,自2008年4月起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某锋于2005年3月7日申请第4524253号“ ”商标,核定使用在第9类的“电线;电缆”等商品上。此外,林某锋还先后在第9类“电线;电缆”等商品上申请“鸽王牌及图”“鸽王”“鸽皇及图”商标,上述商标均因与鸽牌公司的第146035号和第3270081号商标构成近似而被驳回或成功异议。2011年8月,鸽牌公司引证第146035号和第3270081号商标,对鸽皇集团的第4524253号“
”商标,核定使用在第9类的“电线;电缆”等商品上。此外,林某锋还先后在第9类“电线;电缆”等商品上申请“鸽王牌及图”“鸽王”“鸽皇及图”商标,上述商标均因与鸽牌公司的第146035号和第3270081号商标构成近似而被驳回或成功异议。2011年8月,鸽牌公司引证第146035号和第3270081号商标,对鸽皇集团的第4524253号“ ”商标向商评委提出无效宣告。2013年4月,商评委认定第4524253号“
”商标向商评委提出无效宣告。2013年4月,商评委认定第4524253号“ ”商标的申请违反当时《商标法》第二十八条及第三十一条,后该裁定因送达、使用证据的程序问题,于2014年4月被北京高院撤销;2016年11月,在第二轮无效宣告程序(商评委重裁)中,在补正程序问题后,商评委仍然适用《商标法》第二十八条及第三十一条,宣告被诉标识无效。后历经行政诉讼一审、二审,2018年5月2日,该商标最终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告无效。林某锋在该案的无效宣告评审和行政诉讼过程中,为了证明被诉标识经过鸽皇集团使用已经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提交了许可鸽皇集团使用该商标的证据,包括显示被诉标识和字号的发货单,以及鸽皇集团宣传销售“鸽皇”品牌电线电缆产品的买卖合同、广告合同及宣传资料、价目表、门店照片及产品照片等。2010年4月22日,重庆市原质量技术监督局在鸽皇集团的仓库内查获标有鸽牌公司字样的电线电缆,经鉴定系假冒鸽牌公司厂名厂址的产品,并对鸽皇集团进行了行政处罚。2018年10月,鸽牌公司起诉鸽皇集团侵害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根据鸽皇集团的法定代表人林某锋在第4524253号“
”商标的申请违反当时《商标法》第二十八条及第三十一条,后该裁定因送达、使用证据的程序问题,于2014年4月被北京高院撤销;2016年11月,在第二轮无效宣告程序(商评委重裁)中,在补正程序问题后,商评委仍然适用《商标法》第二十八条及第三十一条,宣告被诉标识无效。后历经行政诉讼一审、二审,2018年5月2日,该商标最终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告无效。林某锋在该案的无效宣告评审和行政诉讼过程中,为了证明被诉标识经过鸽皇集团使用已经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提交了许可鸽皇集团使用该商标的证据,包括显示被诉标识和字号的发货单,以及鸽皇集团宣传销售“鸽皇”品牌电线电缆产品的买卖合同、广告合同及宣传资料、价目表、门店照片及产品照片等。2010年4月22日,重庆市原质量技术监督局在鸽皇集团的仓库内查获标有鸽牌公司字样的电线电缆,经鉴定系假冒鸽牌公司厂名厂址的产品,并对鸽皇集团进行了行政处罚。2018年10月,鸽牌公司起诉鸽皇集团侵害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根据鸽皇集团的法定代表人林某锋在第4524253号“ ”商标无效宣告行政诉讼案件中提交的财务资料所载明的营收数据,并综合考虑侵权的规模、持续的时间、恶意等因素,确定了1000万元的判赔额。鸽皇集团不服一审判决,先后提起上诉和再审申请。二审、再审法院经审理,均维持了一审判决。
”商标无效宣告行政诉讼案件中提交的财务资料所载明的营收数据,并综合考虑侵权的规模、持续的时间、恶意等因素,确定了1000万元的判赔额。鸽皇集团不服一审判决,先后提起上诉和再审申请。二审、再审法院经审理,均维持了一审判决。一、关于注册商标被宣告无效前的使用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被诉的“鸽皇GE HUANG及图”商标曾系注册商标,被诉侵权期间覆盖了该商标曾有效的整个期间。本案一、二审程序中,鸽皇集团均提出被诉商标曾系有效注册商标,在其被宣告无效前,鸽皇公司一方的使用行为不构成侵权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笔者认为,从商标法47条“自始无效”的规定和涉及侵权商标曾系注册商标的司法判例来看,注册商标被宣告无效前的使用应承担赔偿责任应无较大争议。
本案一审判决认为,被诉“鸽皇GE HUANG及图”标识虽曾为注册商标,但该商标已被宣告无效,根据2013年《商标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该注册商标专用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原告商标早在2002年就已经被认定为重庆市著名商标,鸽皇集团作为重庆市的同行业经营者应当知晓,但其仍于2005年开始将与之高度近似的、尚未经核准注册的“鸽皇GE HUANG及图”标识使用在电线电缆产品的发货单上,鸽皇集团对曾经的“鸽皇GE HUANG及图”注册商标并无信赖利益可言,因此侵害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二审判决认为,“鸽皇GE HUANG及图”商标与鸽牌公司在先注册商标属于近似标识,被商评委宣告无效,并经北京高院终审行政判决所确认,该商标被宣告无效后其商标专用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鸽皇集团在“鸽皇GE HUANG及图”商标被宣告无效前的商标使用行为失去了合法性及定当性,且该期间应当作为确定鸽皇集团赔偿金额的考量因素。
二、关于侵权诉讼时效和赔偿时效(赔偿计算期间)
本案中,鸽牌公司主张的侵权赔偿计算期间为自鸽皇集团最早开始侵权行为的时间(2005年)至本案起诉前(2017年)的持续期间共13年。鸽皇集团在一、二审均抗辩称鸽牌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诉讼时效,即使法院认为侵权成立,鸽皇集团应只对鸽牌公司起诉前的“两年”期间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一审审理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2号)第十八条规定,“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超过二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持续,在该注册商标专用权有效期限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二年”在修改后的法释【2020】19号第十八条规定中已改为“三年”),2017年《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民事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包括“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2021年《民法典》的规定与之相同);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此规定在2020年修订的法释【2020】17号中被保留)。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3号)第一条规定,“原告以他人使用在核定商品上的注册商标与其在先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为由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告知原告向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申请解决。”(截至目前虽已有多件涉及驰名商标对抗在后注册商标侵权的司法判例,此规定在2020年修订的法释【2020】19号中仍被保留)
梳理上述规定可以理解,首先,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规则,本案涉及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为三年而非两年;其次,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向前推算”三年计算有其适用的逻辑前提,即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也就是说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则不存在“向前推算”的问题,而本案存在注册商标侵权与确权纠纷民行交叉和衔接,涉及诉讼时效中断问题。本案一、二审法院均认为,自鸽牌公司于2011年向商评委提出涉案第4524253号商标无效宣告申请时起本案民事诉讼时效中断,直到2018年5月2日北京高院作出无效宣告的终审判决,自该行政诉讼终结时起,鸽牌公司的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同年10月12日,鸽牌公司提起本案之诉符合原《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因此在未过“三年”诉讼时效的情况下,因侵权行为仍然在持续,赔偿时效不受“三年”限制,一、二审判决支持了鸽牌公司以被诉注册商标被宣告无效前后共计13年的侵权持续期间累计计算侵权赔偿数额的主张。
三、关于侵权赔偿数额计算方式
《商标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确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的顺位,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为第二顺位。本案一审审理时有效的法释【2002】32号司法解释(及2020年修改后的法释【2020】19号)第十四条规定了“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商品单位利润乘积计算,此规定与最高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的法释【2015】4号(及2020年修改后的法释【2020】19号)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该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笔者以为,上述规定其表述可理解为侵权产品的合理“销售利润”,对工业企业而言,产品销售利润在财务数据上可体现为“主营业务利润”。
本案,鸽牌公司主张鸽皇集团13年侵权期间(2005-2017年)的累计侵权获利总数额177,293,034.74元,即是以该期间鸽皇集团各年度的“主营业务利润”为计算基准或依据,包括(1)林某锋在第4524253号“鸽皇GEHUANG及图”商标争议程序中提交的加盖有鸽皇集团印章的财务报告,显示鸽皇集团2008年至2013年度主营业务利润总额为171,564,936.11元;(2)鸽牌公司查询到的鸽皇集团2005年至2007年期间的主营业务利润总额428,633.83元;(3)鸽牌公司查询到的鸽皇集团2014至2017年期间的主营业务收入总额105,437,000元,参照依据《中国电器工业年鉴2015》公布的电线电缆行业利润总额与主营业务收入计算出的行业主营业务利润率,计算出的鸽皇集团2014年至2017年期间获利总额5,299,464.80元。
一审判决根据鸽皇集团2005年至2013年期间的累计主营业务利润总额高达171,993,569.94元,确定鸽皇集团自2005年以来的侵权获利数额高于鸽牌公司请求赔偿的1000万元,认为无须适用惩罚性赔偿,鸽牌公司请求赔偿的数额应予全额支持。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综合考虑鸽牌公司涉案商标的知名度、鸽皇集团的主观恶意、侵权情节及获利等因素,全额支持鸽牌公司的赔偿请求,并无不当。
四、关于商标争议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在民事案件中的采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根据诉讼诚信原则,当事人在商标争议程序中提交的涉案商标使用证据,可以被对方当事人在民事案件中直接作为指控侵权、主张侵权赔偿的证据。
本案中,鸽牌公司即是充分利用了被诉商标评审及行政诉讼程序中林某锋提交的使用及知名度证据(包括被诉侵权产品发货单、销售合同、发票、广告合同及宣传资料、价目表、门店及产品照片、财务资料等),并对该等证据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统计。例如,该案判决书记载“林某锋提交的销售合同及发票显示,2005年至2016年期间鸽皇集团销售电线电缆产品的客户区域分布包括重庆各区县、四川、湖北、贵州、上海、云南、辽宁、山西、广东、安徽、天津、内蒙古、福建、江苏等省市”;“林某锋在第4524253号‘鸽皇GEHUANG及图’商标评审及行政诉讼程序中提交了由鸽皇集团出具的财务资料,其中《损益表》显示鸽皇集团2008年至2013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总额1240862635.24元,扣除主营业务成本、经营费用、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后的主营业务利润总额为171564936.11元”。该等证据系一、二审法院据以认定鸽皇集团侵权情节及获利的重要证据,其中鸽皇集团的财务资料则是法院采信的认定赔偿数额的核心证据之一。对于鸽皇集团提出该证据不应被采信的抗辩,二审法院认为,“由于林某锋在提交前述财务资料时系鸽皇集团的法定代表人,且财务资料上加盖有鸽皇集团的公司印章,能够推定该财务资料系鸽皇集团制作或提供,至少也应当知晓;但是,鸽皇集团有能力却未举示证据进行反驳或推翻该财务资料,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财务资料中《损益表》载明的财务数据能够反映鸽皇集团的实际经营情况并无不当。”
本案是一起通过无效宣告程序来辅助民事侵权的案件。鸽皇集团在无效宣告案件和侵权案件中,均提供了大量的推广宣传和使用证据,以通过“市场格局”进行抗辩。鸽牌公司通过强调“鸽牌”商标的知名度以及鸽皇集团注册和使用“鸽皇”商标和字号的恶意,明确“市场格局”抗辩的前提是该“市场格局”是善意、诚信经营形成的,在被诉标识存在恶意申请、攀附性使用的情况下,即便其有一定的市场规模,也不应被保护;如承认此种行为所形成的所谓市场秩序或知名度,无异于鼓励同业竞争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罔顾他人合法在先权利,强行将其恶意申请的商标做大、做强。
本案还明确了在商标侵权案件中普通诉讼时效和赔偿时效之间的关系。随着《民法总则》的施行,诉讼时效从“两年”变成“三年”。《民法总则》第195条规定,权利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或与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时,诉讼时效中断。本案中,鸽牌公司于2011年向商评委提出商标无效宣告申请,诉讼时效中断 ;直到2018年5月,北京高院作出无效宣告的终审判决,诉讼时效起算。从2018年5月至起诉时的2018年10月,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在未过普通诉讼时效的情况下,侵权行为仍然在持续的,赔偿时效不受“三年”的限制。
”商标,由鸽牌公司的前身重庆电线厂申请,于1981年4月15日核准注册,核定使用在第9类的“电线”商品,2002年4月25日转让至鸽牌公司名下。该商标于2002-2014年期间多次被原重庆市工商局认定为重庆市著名商标,2010年1月15日被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此后,该商标在2018年期间多次在商标异议、商标无效程序及行政诉讼中被作为驰名商标进行保护,“
”商标在多个生效判决、裁定中被认定驰名的时间点为2008年1月开始至今。第3270081号“
”商标、第16039215号“
”商标均由鸽牌公司申请注册,核定使用在第9类“电线;电缆”等商品上。
”商标,核定使用在第9类的“电线;电缆”等商品上。此外,林某锋还先后在第9类“电线;电缆”等商品上申请“鸽王牌及图”“鸽王”“鸽皇及图”商标,上述商标均因与鸽牌公司的第146035号和第3270081号商标构成近似而被驳回或成功异议。
”商标向商评委提出无效宣告。2013年4月,商评委认定第4524253号“
”商标的申请违反当时《商标法》第二十八条及第三十一条,后该裁定因送达、使用证据的程序问题,于2014年4月被北京高院撤销;2016年11月,在第二轮无效宣告程序(商评委重裁)中,在补正程序问题后,商评委仍然适用《商标法》第二十八条及第三十一条,宣告被诉标识无效。后历经行政诉讼一审、二审,2018年5月2日,该商标最终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告无效。林某锋在该案的无效宣告评审和行政诉讼过程中,为了证明被诉标识经过鸽皇集团使用已经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提交了许可鸽皇集团使用该商标的证据,包括显示被诉标识和字号的发货单,以及鸽皇集团宣传销售“鸽皇”品牌电线电缆产品的买卖合同、广告合同及宣传资料、价目表、门店照片及产品照片等。2010年4月22日,重庆市原质量技术监督局在鸽皇集团的仓库内查获标有鸽牌公司字样的电线电缆,经鉴定系假冒鸽牌公司厂名厂址的产品,并对鸽皇集团进行了行政处罚。
”商标无效宣告行政诉讼案件中提交的财务资料所载明的营收数据,并综合考虑侵权的规模、持续的时间、恶意等因素,确定了1000万元的判赔额。鸽皇集团不服一审判决,先后提起上诉和再审申请。二审、再审法院经审理,均维持了一审判决。